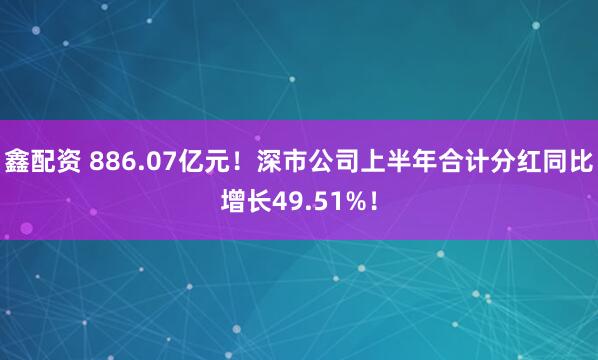蒋元顺匠心智策
1956年,大西南的工业建设项目开展得热火朝天,父亲和300多个家乡青壮年放下手中的农具,用一根扁担挑上破烂的被子、几件换洗的单薄衣服、20来斤路上吃的口粮,从老家四川简阳步行31天、1500多里路,历经了不少艰险,终于到了现在的西昌会理益门煤矿。
矿山里一年到头吃的是煮黑豆、玉米蒸馍,住的是低矮潮湿、用稀泥和石头垒的本地居民称之为“干打垒”的土房子。矿工从井下归来,一身灰,认不清谁是谁,只能看见两只眼睛在转动,还有白森森的牙齿。没有澡堂,只好用脸盆洗澡,一盆、两盆、三盆……洗出来的水黑如墨汁,身上自然也是洗不干净的。
在我4岁时的一个晚上,我们一家人还在“干打垒”里沉睡,凌晨5点来钟被人敲门吵醒,得知父亲在井下受伤了。一家老小哭喊着来到医院,看见一身煤灰的父亲躺在病床上。脾气火爆的父亲嘴里叼着一支“兰花”旱烟,见我们便大骂,嫌我们哭闹得心烦。母亲见此情景,破涕为笑。见多了矿山事故的我们,还能看见父亲发火骂人,是多么幸福呀!
小时候,我最爱去井口旁的烤火棚。等送馒头的人挑着两大筐“班中餐”来,省吃俭用的父亲凭票给我们姐弟四人一人买一个大馒头吃。这在我们眼里,可是世界上最美味可口的食物。懂事的哥哥、姐姐匠心智策,总要在我们的馒头上掰一小坨,用纸包好,拿回家给妈妈吃。
小学三年级时,有一次,我邀请最要好的同桌一起去那个烤火棚玩。烤火棚里正烧着从井下拉回来的烂木头,浓烟熏得人直流眼泪。父亲和工友们推着沉重的矿车,气喘如牛地出了井口。我看见父亲和工人叔叔们都一丝不挂,顿时羞得无地自容。父亲见了我和同学,忙去把衣服穿上,向我解释说:“你不知道,洞子里热得很,穿上衣服一会儿就被汗水浸湿了,身上风湿重,骨骼就会麻痛,很不舒服。”我心里在默默流泪。吃了馒头,我眼含泪花地要同桌和我拉勾保证:不准把父亲没有穿衣服推矿车的事给任何人说,不然不和他做朋友!
父亲闲时会去河里钓鱼,还会背上火药枪上山打野兔、野鸡,为的是能改善一下生活。父亲唯一的爱好,就是每天能喝上一两杯没有下酒菜的“寡酒”。后来生活好一些了,有了炒花生、米花糖、麻花这些下酒菜,但这些都被眼馋的孩子们分享了,父亲也只是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吃,高兴地喝着小碗里的“寡酒”。
1976年,唐山大地震后,许多地方都在“躲地震”。父亲从山上砍了竹子,找来一块空地,搭建起“地震棚”。下班后,他就在“地震棚”旁的荒地上开荒种菜。父亲种的南瓜特别好吃,嫩南瓜我们一家人吃不完,就拿到菜市场去卖。秋天,老南瓜成熟了,一个有二三十斤重,蒸熟吃特别香甜可口,父亲会送一些给矿上的工友。在那个年代,我们一家有吃有穿,全靠父亲像牛一样,上班在井下劳动,下班回家种菜喂猪。
父亲还给我买了三只小鹅,他说鹅养大了,卖的钱我可以拿去书店买书。每天放学后,我就赶着鹅去吃草,鹅不停地找青草吃,吃饱了就安静地听我给它讲故事、朗读课文。我们家在“地震棚”一住就是7年,后来才搬到矿山单身宿舍,挤在一间30多平方米的房子,姐姐哥哥一直住到结婚安家另外找新房。
1980年,我的矿工父亲退休了。由于在井下工作了几十年,他患了风湿,一到春季和冬季关节就痛,步履艰难。很多时候,去矿区逛逛散心,都是我最小的兄弟老七背着他去。父亲在我心里就像会理老家山顶上的一株老松树,经历沧桑,但仍能傲霜矗立。
自小学五年级起,我就喜爱文学,读小学四年级时,就给成都的《红领巾》杂志投稿,并发表了几篇小故事,后来又陆续发表了一些作品。2016年大年三十晚上吃团圆饭时,父亲突然跟我说:“老三,这大过年的,你不能说个不字哈!我们一家人早就知道你写了几十年就想出一本书。你要用心写一本关于益门煤矿的书,让后辈儿孙记住益门煤矿的历史和矿工的艰辛。”
我看着苍老的父亲,千言万语哽在喉头,却说不出一句话来。此时,我多想伸手替父亲擦去那深深皱纹里镌刻的煤灰,但那煤灰已渗入他的肌肤和血液,再也抹不去了。我的眼泪拼命向外涌,我背过身去,使劲儿将它们劝回眼眶去,因为父亲说大过年的,哭是很不吉利的。
我的矿工老父亲啊……看似平凡,却有一颗像所有矿工一样坚韧、仁爱、高尚的心灵。我暗下决心,一定要完成父亲的心愿匠心智策,用心书写煤矿工人的生活和工作点滴,我要为下一代了解父辈和煤矿历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,以告慰父亲一生的辛劳与爱。
富通优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